十多年前我曾去过三次郑州,不过大抵都来去匆匆,偶有一次稍得闲暇,问起郑州有何去处值得一游,便见东道主面露尴尬之色,我急忙把话题岔开。印象中当时盛夏六月,满城的法国梧桐遮荫蔽日,此外就只记得一路过去看不到什么有点历史感的老房子,仿佛这座城市是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新长出来的。
通常去一个异乡城市旅游,游人总是本能地去往当地的老城,因为那里往往沉淀着最具代表性的当地文化。然而在这里,“老郑州”一词差不多像是个矛盾修辞。
直至清末,郑州都一直只是开封府下辖的一个小县(郑县),县城人口不过近2万人,但1909年汴洛铁路在此与1906年通车的京汉铁路交汇,它自此便像哈尔滨、石家庄一样,作为铁路交通的枢纽而迅速繁荣起来,一时所谓“纷华靡丽,不亚金陵六朝”。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郑州城是一座历史极为浅短的城市,在很长时间里主要以其工人斗争的革命传统著称,然而现在,它却又处处自称为古都。尽管国内不少城市也有相似的状况,但似乎很少有像郑州这样,其城市自我形象中,古都、红色传统、现代化城市三个明显存在断裂的部分截搭在一起——借用甘阳的术语,郑州需要城市形象上的“通三统”。
一到郑州便不难发现当地特别钟爱“中原”、“中州”、“天下之中”这些语汇,地铁通车要强调是“中原首条地铁”(当然,还能是哪个城市?),地铁标志是饕餮纹状的“中”字,连机场出来的收费站顶部也标着一行闪闪发光的金字:“中州第一门”。
在河南博物院(1998年由“河南博物馆”更名),更是处处可见“中原”——据其简介单页,河南博物院意在“汇集历代文物瑰宝,一展中原流金岁月”,是“以大量实物展示为基础,反映中原这一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心地域的文明进程与重要文明成果,再现中原文明的延续性、包容性和影响力”。
在“华夏古乐”的单页上更明白指出:“河南博物院是中原传统文化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的中心”。这里的“中原”并不只是地理名词,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文化认同和自我意识——即河南是“天下之中”,也应回复到那种辉煌的中心地位,自然,郑州又是河南的中心。
大概正因此,在网上偶尔能看到极端者将北京列为河南的主要对手,理由是“北京害怕河南夺回政治中心,北京满族害怕汉族团结在河南的周围,北京媒体一直是妖魔化河南的主力。只是大多河南人不知道。”从这一点上来说,河南之于中国,大概正如中国之于世界。
在河南博物院的十八个展厅中,基本陈列“中原古代文明之光”占了其中八个厅——先秦四个、两汉魏晋南北朝两个,隋唐、宋元各一。正如陕西博物馆突出周秦汉唐四朝(基本只围绕着长安一个城市),这一布展的结构安排所呈现的“中原叙事”也极大地偏重本省历史上最辉煌的早期时代。
给人的印象,仿佛中国文明的火炬自最初起,在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洛阳、开封(偶尔再加上许昌)之间来回传递,河南境内的城市不断地继续着这场接力赛,直到到九百年前北宋东京城的梦华消歇,之后河南便无故事可讲。
在先秦时代使用的都是诸如“宅兹中国——洛邑的建立”、“天下枢机(英译为The Heartland of the Universe)——郑卫之地”这样的词汇,而1127年开封的繁华结束之后,便只剩下尉氏县元墓壁画、宋元戏曲文物等寥寥物件,以及一个收藏着些许二流文物的“明清珍宝馆”。
在这样的印记里,远古、中古都比近古更为清晰可见,博物馆里复原的《清明上河图》立体图、北宋东京城模型以及机场的“大宋官窑”,以及郑州城不时可见的商文化符号(包括地铁站里的饕餮纹),都使人想象一千年前甚至三四千年前要比两三百年前还容易得多。
郑州 河南博物院 北宋东京城复原效果图
这正如《希腊的现代进程:1821年至今》一书中所谈到的,现代希腊国家对自身与古希腊的明显差异和断裂置之不理,坚持将古希腊作为国家神话的主要部分,“是因为启蒙后的欧洲暗含着的标准就是:古代希腊在认定新国家正统地位时起决定性作用”,而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和历史不仅是通往过去的、值得尊敬的道路,而且还对培养过去文明历史的意识以及解决现代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由此一来,在雄心勃勃地要按照自己想象的民族历史重塑现代的人们来说,考古学和历史就成为他们实现计划的工具。”
2000年我曾去过一次洛阳,由于怀着无数对古都的想像,结果在那里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幻灭,那时才意识到,一个历史地名的延续性往往遮蔽了太多断裂:现实中的洛阳,与其说是“九朝古都”,不如坦率地承认它主要是一个近半个世纪里建立起来的军工城市。
郑州或许犹有过之,毕竟这里遗留下来的古代建筑仅有城隍庙和文庙而已,而即便这两处,一度也疏于保护,在2000年修缮前,郑州文庙已仅残存两座大殿。想来部分也因此,早些年的郑州城市地图上都很少标出本地这仅有的两处值得一提的明清古迹。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现代郑州随铁路贯通而勃兴时,它是一片无历史之地。虽然“郑州”之名由来久远(“郑”原在今陕西华县,西周末年犬戎入侵,郑人乃分两支出奔,一支在河南建立郑国,是为新郑;一支南逾秦岭,即今汉中南郑县。唐宋时的几百年间,“郑州”在陕西而“郑县”在河南),但那大抵就像两河流域的那些古城一样,除了少量文字记载和一些文物残片,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之间并无延续性。
作为古都的郑州乃是一项现代发明,和它的红色传统一样起源于1920年代,那些年里接连了发生了几件对这座城市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同年北洋政府正式将郑县辟为商埠;1928年冯玉祥改郑县为郑州市,其城市地位首次得到承认;1921年发现仰韶文化和1928年发掘殷墟则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的诞生,正是这促成了后来郑州商城的发现,以及郑州对自身的重新认识。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铁路、公路网建设中,郑州与北京、武汉是最明显的全国路网枢纽,也极大地得益于此。铁路连通后它一度在经济上依附于汉口,但陇海铁路的延伸和1929年起的世界大萧条打击了汉口的转口贸易,原本集中于郑州后沿京汉铁路南运的陕豫货物改道向东,郑州渐渐摆脱汉口而自成一大都市。
1934年,张恨水在《西行小记》中说:“在三十年前,郑州火车站边,不过是几十家草棚子而已。现在可了不得,一望也是几层楼的高大洋房。……你若是西行的人,到了郑州,就得想一想,有些什么旅行必备的东西,买了没有。假如是没有买的话,可以在这里买齐。因为到了西安,虽然也买的着,有的不好,有的太贵。”他又说:“到了洛阳,就是内地了,一切物质文明,去郑州很远。”
这些话都可见郑州作为新兴商埠已超越洛阳、西安等西部大城市,其对洛阳的优势自此再未改变,所谓“洛阳一条线,郑州一大片”,即指洛阳仅一条大街可称繁华,而郑州则是连绵的城区。1949年郑州全城人口15万,在河南省仅次于当时的省会开封(24万),但很快便在五年后取代开封成为河南省会。
在这急骤的现代化进程中,郑州主要被视为一个交通枢纽、货物集散地,乃至鱼龙混杂的人口贩卖中心(据1921年华洋义赈会报告),二七大罢工和总工会之所以能在这里组织起来,或许也是因为铁路工人们在这里彼此都面临着一个陌生的城市环境。
那时没有人认为它是文化中心,更别提“古都”了。“古都”叙事的吊诡之处在于,它看起来是这座城市最早的一个段落,但却是郑州三部分自我形象中最迟拼接进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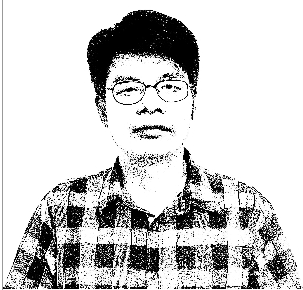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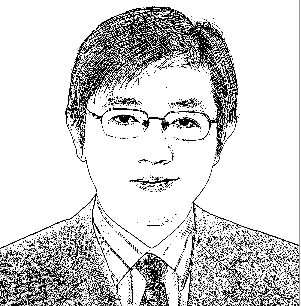






.gif)
.gif)

